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卡尔·雅斯贝尔斯把公元前500年前后,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古希腊)和印度等地区的人类文化发展现象称之为轴心时代。自20世纪60年代后,这一理论已引起了中外思想家和社会学家的普遍注意。不仅如史华兹和艾森斯塔特等西方人文学者以此为论说之据,而且中国(包括华裔)学者也屡屡提及这一观念,特别是广义的新儒家,谈到先秦思想,几乎必称“轴心时期”。对轴心文明的信奉者而言,在公元前800—公元前200年这六百年期间,希腊、印度和中国三大古代文明,都曾先后以不同的方式经历了哲学的突破阶段。所谓哲学的突破,即对人和世界的认识都达到了一种飞跃, 雅思贝尔斯曾对此作了如下论述:“这个时代的新特点是,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询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1]这种思想状况以前未曾有过。余英时曾作《轴心突破和礼乐传统》,提出了中西文化内向超越和外向超越的思想,而内在超越与轴心时代,则成为思想界的套语(关于“内在超越”所涉及的理论问题,作者在他处已论及,这里从略)。

世界历史并非仅限于公元前800年,轴心理论同样也被赋予不同形态。在认同轴心时代的学人看来,科学技术正在催生一个不同于以往轴心时代的状态,而走向所谓第二轴心时代。人类似乎由此经历了两个轴心时代,即与公元前500左右的第一轴心时期有所不同的第二轴心时期。尽管第二轴心的提法多见于当代,但雅斯贝尔斯事实上也已提及:“第一次轴心世界的纯正清晰和清新诚朴并没再现,一切都处在严格的传统的阴影之中,都遵循一条不真实的道路。尽管有这些错误的方面,但那些伟大孤独的人物,都设法获得了最非凡的成功。然而另一方面,第一次轴心世界并不知道第二次轴心世界,可能性向第二次轴心时代敞开着,因为第二次轴心世界多样的意义和更加为此,第二次轴心世界可能接受第一次轴心世界的经验以及适合于它的思想,所以它一开始就有更加多样的意义和更加巨大的精神财富,” [2]尽管第二轴心时期与科技时代相关,但轴心世界仍被视为普遍现象。
第二轴心的提法,无疑使轴心时期或轴心时代的概念进一步强化了。然而,以“轴心时代”为视域,显然有其问题。一些学者似乎也注意到此,但其关注点可能未体现实质的方面。以当代的学人而言,龚鹏程便认为,轴心时代的提法的主要缺陷,是将孔子以前划为原始神话时代,并把殷周文明看作是原始蒙昧时期,认为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才进入精神飞跃的时代。这类说法与“截断众流”“周文疲弊”流行之论一样,是一种“历史断裂观”,而所谓轴心时期,其实也就是这样的理解在古代的再现:文明在变革以前,尚停留在人的自我意识尚蒙昧不清的阶段;变革以后,精神自我醒觉了,遂产生了飞跃的进步。[3]这一批评固然有见于“轴心时代”的概念不合思想演化实际,但以“原始文明”与“精神飞跃”之分等为其问题所在,显然未能把握问题的根本或实质。
从语义上看,“轴心”意味着以某一点为环绕的中心,它所蕴含的是围绕相关之点而变迁,其内在意蕴则是循环、重复。按其实质,以“轴心”为主导,侧重的是在某一个固定之点旋转,其特点是仿佛在一个圆圈里循环、往复地活动,始终无法越出这一圆圈,也永远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前进。轴心时代同时蕴含某种目的论:轴心之前的文明以轴心为目标而趋近之,轴心之后的文明发展同样以此为指向而回归以上目标。它的背后似乎蕴含着宗教(基督教)意义上的目的论,这与上述观点的西方视域相关:如果我们从“轴心”这样的角度去理解文明的发展历程,那么,文明的发展似乎仅仅是围绕着某个既定的出发点不断地打转,这一被视作固定不变的出发点,又同时被默认为以西方为中心。可以看到,所谓“轴心时代”,乃是在原有的框架内徘徊不前。就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文明应当被看作是一个持续演进的过程,其演化是不间断且朝着更高阶段发展的。但这种发展,绝非以某一不变的“轴心”为固定之点而循环、往复。可以说,从其开端起步而不断前行,构成了文明发展的现实形态。
按其本义,“轴心”与静态之域相关,注重于将相关对象纳入某种界域;开端则涉及动态的过程,其关注之点是变化之流。思想的演化诚然无法离开一定的领域,但它总是处于变化的过程之中,而每一次变动及其结果,都为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出发点。这种出发点既表现为阶段性的开端,也构成了继续前行的起点。如果执着于“轴心”,则往往会限定于一定界域而忽略发展之流。世界文明的演化,确实在古希腊、古印度、先秦(公元前500年前后即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经历了重要的历史衍化,此后的发展也无疑以此为起点,但如上所言,这种发展,绝非以某种“轴心”为参照之系而凝固不变。如上所述,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个起始点或“轴心”,可以看作是文明发展的开端或阶段性的出发点。文明从这一开端启动,一路向前推进发展。这样,对文化的发展,更为准确恰当的看法应当是文明前后的发展与文明的进一步拓展和延伸,或者说,从一个阶段性的全新起点或新的开端出发,持续演进。只有这样理解,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地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和桎梏。反之,如果依旧深陷于 “轴心时代” 的固有观念中打转,那么文明的发展就将永远停滞在原地。可以看到,对中国和西方思想历史演进的理解,应当超越“轴心”的概念。
[1] 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8-9页。
[2] 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89页。
[3] 参见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1102/08/7322862_700191703.s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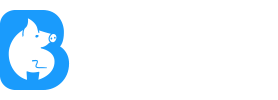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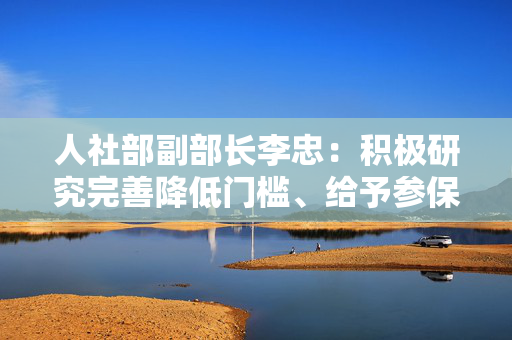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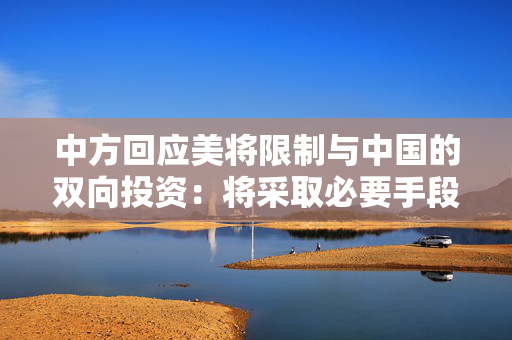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