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出生的我,对家的认识,是从老乡身上学到的。

我的老家山东菏泽巨野县,往西不远,就是河南兰考。
小时候的夏天,我有时和种瓜的老爷爷住在瓜地里,惬意,过瘾。为啥呢?可以学手艺。什么地种瓜,什么地种花生,哪种瓜喜水,哪种瓜喜旱,都是跟种瓜的老爷爷学的。要是住在打麦场,我就跟开拖拉机的叔叔们学几手。白天,跟他们学怎么犁地;晚上,跟他们睡一个炕上。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像一家人。
1975年3月8日,我在二炮7784部队战士业余宣传队光荣入党。当天,我给在贵州凯里的父母发电报说:“爸爸妈妈,我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母亲很快回了一封电报,三个字:“好好干!”高兴、祝福、希望,他们所有想表达的感情,都在“好好干”三个字里。
我的岳父是国民党军起义的军官,他人生的最后几十年一直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70岁时终于如愿。到老年时,他的视力退化严重。他是用收音机听完了电影《焦裕禄》,还写了一篇《我听〈焦裕禄〉》。这是对我这个晚辈极为深沉的爱,我很感动。
岳父问我,焦裕禄的孩子是谁演的?我说,都是当地老百姓的孩子。他又问,焦裕禄要住院了,老百姓去送他,那个场景有上百人吗,是演员吗?我说:有100多人,都是当地老百姓。当年送过焦裕禄的老百姓,听说要拍焦裕禄的电影,把自己的子女送来参演。演的时候,导演不用说戏,当时是什么情景,该穿什么衣服,手里该拿什么东西,他们的父母早早就交代清楚了。仔细想想:这不就是家风、家教吗?这上百人的场面,背后又是多少个普通人家呢?
什么是家?看看我们的汉字就知道了。几千年前的甲骨文里,“家”的上半部分就是“宀”,说明家是遮风避雨的地方。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家”的写法略有不同,但总是象征着安定和温暖。
我喜欢演戏。生病那段时间,看人家演戏,我眼馋、着急。一吃上剧组的盒饭,就不闹心了,感觉自己的生命还有价值。我的每一个角色,都有家人的支持。
我的爱人海丹当过演员,是我演新戏的第一个观众,也是十分苛刻的观众。评价我的艺术创作,她一点都不客气。她最不满意我演的冯石,因为当时我没有下决心减肥。能做到而没有做到,不可原谅。放疗的伤害,给我带来了严重的口腔后遗症,影响了念台词。她找了很多书,“强迫”我每天练习说话。长的文章,一天念好几遍,短的文章,一天也念好几篇。
我生病的时候,儿子正读中学。他的妈妈要照顾我,他只能跟姥姥住在一起。读初二时,他在作文《家》中写道:“这就是我的家,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温暖、帮助、自信的地方。”我对儿子有亏欠。或许,他在那时候失去的,终将成为一笔金钱换不来的财富。
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讲述真善美的家风故事,是文艺工作者的职责。小时候,我最喜欢看小人书《岳母刺字》。岳飞跪在地上,岳母在他的背上刺下“精忠报国”四个字。这幅画面,记忆犹新。我看的第一部电影是《自有后来人》,走出县城电影院,李铁梅、李玉和、奶奶的形象在我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他们塑造了我对革命家庭的印象。
回头看,我演过的人物,很多都与家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戏里面,中国人的家庭、家教、家风多多少少有所体现。
我在《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里演周文王。他希望自己的国家富强,希望人民过上好日子,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够离开朝歌,他承受了人类无法承受的奇耻大辱。从周文王身上,可以看到3000多年前中国人的家风。
我演过李大钊。小女儿去世,他很悲痛,但他没有扑向女儿的身体,而是哭都哭不出来。走进法庭,他突然听到孩子们叫“爸爸”,很意外,又尽量让自己保持镇定。李大钊是革命者,也是充满深情的丈夫和父亲,他是早期革命领袖,也是随时准备赴死的战士。因为他知道,他的小家与国家紧密相连。
杨善洲退休了,没有在城里养老,而是选择上山种树。朋友劝他,他说:共产党人的职业病就是自找苦吃。自找苦吃的不只是他自己,也包括他的家人。电影《杨善洲》里面,他的爱人有一句话:咱们的杨书记不是咱们家的书记,是老百姓的书记。的确如此。女儿想要一个城市户口,杨善洲没有答应。后来,女儿在给他的一封信中写道:你这样做,我们都理解,但作为你的孩子后代,我们也不容易。读了这封信,杨善洲一宿没睡。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今天,杨善洲的女儿女婿们仍是普通的农民、工人、乡村教师。他们默默做事,没有人沾杨善洲的光。
我还演过外交官。在《万里归途》中,我演的外交官无论如何都要把同胞带回祖国,这是他们的职责和使命。因为,祖国就是我们的家。
作为普通人,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体现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家人、我们的身边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大家一起作贡献,我们的国家更好了,民族富强了,小家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每个人的小家,都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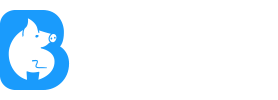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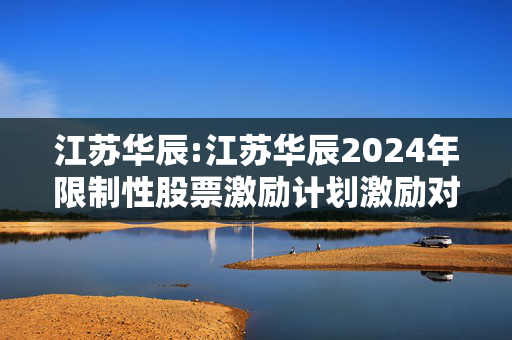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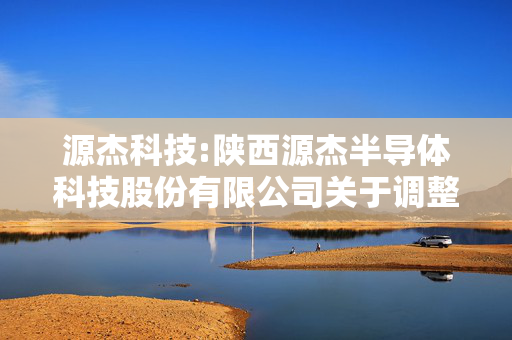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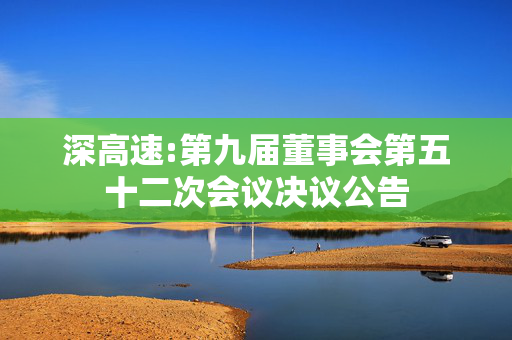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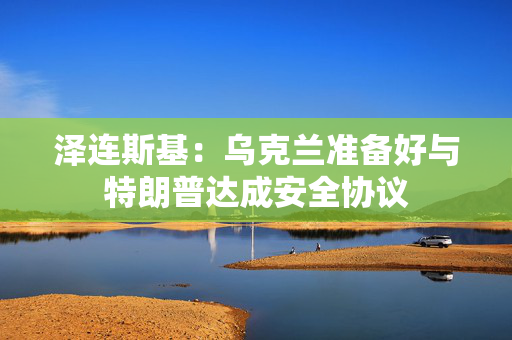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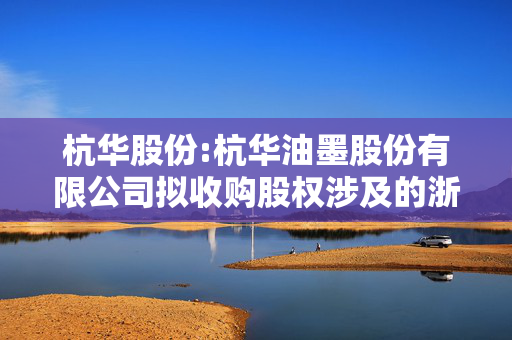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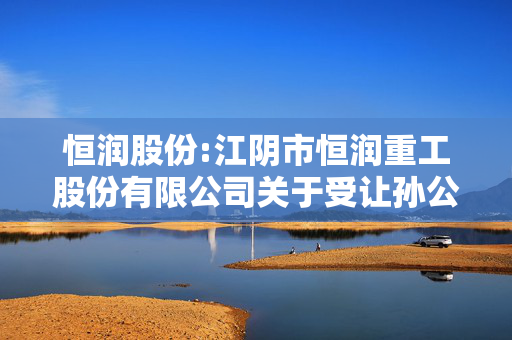
发表评论